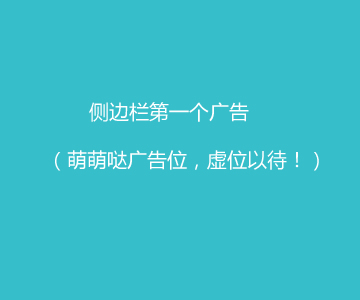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原题目《人类学家张劼颖:“我做垃圾分类也没用”这种话,在某种水平上是推卸责任|专访》,题图来自:IC photo
“拾荒者”这个名字道尽了它所指涉的谁人群体被不停污名化、边缘化的处境:他们是都市剩余物的捡拾者,依赖住民天天甩掉的垃圾为生,不事生产,故而是可耻的;他们与肮脏、腐臭的垃圾为伍,故而被光鲜亮丽的都市同垃圾一道,流放于都市文明之外的荒原。
在这个不生产、不消费即是有罪的天下,他们没有直接介入工厂的流水线作业,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便没有他们的功勋,没有为都市孝敬大量的消费额,自然也就不被其接纳和迎接。
但一个令人羞愧的事实是,臭气熏天的垃圾恰恰来自整齐的餐厅、阛阓与住宅,拾荒者并非是街角臭气的罪魁祸首。相反,他们通过劳动重新规整了混沌与污浊,维系了都市的运作。若是没有拾荒者的存在,大量可以接纳再造的废品将会被直接倾入垃圾填满场与焚烧炉,造成伟大的资源虚耗。
十余年前,鲜少有人关注垃圾问题与拾荒者的劳动和生涯。这两年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紧迫,垃圾分类、资源接纳等议题获得越来越多的讨论。继上海强制推行垃圾分类接纳后,今年5月1日起,北京也正式加入了垃圾分类接纳的行列。对拾荒者而言,垃圾分类是否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在资源接纳中到底饰演什么样的角色?
克日,界面文化采访了《废品生涯》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博士,与她聊了聊那些与垃圾打交道的人、垃圾分类的逆境以及垃圾的宿世今生。
2008年起,张劼颖最先与《废品生涯》的另一位作者胡嘉明博士在位于北京六环外城乡接合部的冷水村睁开野外考察,实验明白垃圾若何影响了冷水村大院的拾荒者劳动、生涯与情绪。
她们在书中指出,与人们对“捡破烂儿的人不起劲、不需要手艺”的印象相反,拾荒者的劳动具有高度的天真性和细微性,他们熟稔关于质料、接纳的知识与市场规则,在“非正式经济”地带积极地钻营机遇。
然而,他们的都市求生又到处受到结构性限制的威胁,无法享受都市住民福利,在子女教育等问题上缺乏保障,每逢都市人口政策更改之际,甚至会遭到驱逐。于是,“老家”成为了拾荒者关于美好未来的的寄寓,与他们在都市当下的生涯形成反差。
在采访中,张劼颖强调,只管拾荒者面临严苛的结构性限制,但他们与其他劳动者一样,都在限制之下积极地施展主观能动性,追求可能。此外,拾荒者、环卫工人群体所遭受的忽视与歧视也与当前的垃圾文化有关。
当生涯的方方面面被开发为消费领域、工厂举行大批量生产、人们崇尚“用完即弃”的消费文化时,我们对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明白被简化为“有用”和“没用”,物摆不脱成为垃圾的宿命,负责处置垃圾的人也被视作腌臜与不洁。无论是要去除这样的私见,照样真正做到垃圾分类接纳,都需要正确熟悉垃圾的发生与处置机制,重新想象人与物的关系。
正在做垃圾分类宣传调研的张劼颖
当下的生产方式注定了大量剩余物的发生
界面文化:在最先做垃圾研究之前,你是若何看待生涯中的垃圾的?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进入到研究者视角的?
张劼颖:在做研究之前,我和通俗人一样,对垃圾没什么稀奇的想法,用完、扔完就以为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我对垃圾的新熟悉是在与研究工具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最初我关注的是人,想看冷水村这群人是怎么生涯的。厥后在考察他们收垃圾时,会突然以为,他们正在分拣的这些器械实在就很像自己昨天扔的,站在那里会最先发生一种想象:这个器械原来在谁的手里?怎么就到了这儿?物主的生涯是怎样的?一个面霜瓶、一个作业本,都是生涯中很常见的。人类学讲社会生命,物成为垃圾之前的生命在那里?好奇心就这样发生了。
不是说在研究之初,我就已经明确了自己要关注垃圾,对垃圾有完全差其余看法。相反,我是作为一个通俗人,带着通俗人的知识和履历去做研究,不停地和研究的工具互动,才发生了新的想象和熟悉。这是社会科学稀奇有意思的地方,你不只是在做研究,研究工具也会改变你。
界面文化:据我领会,你的研究主要关注物酿成垃圾之后的故事,好比说去看拾荒者、垃圾焚烧厂。你适才提到“物的履历”这个观点,实在这些垃圾在成为垃圾之前另有一段很主要的履历,你对这个“前半段”有关注吗?
张劼颖:这部门内容我也在做,但还没有泛起出来,也需要做更多研究。
我现在关注得对照多的照样物酿成垃圾、即将酿成垃圾的瞬间,也就是我们扔或不扔、垃圾分类做或不做的瞬间。这个瞬间界定了此物是不是垃圾,也界定了什么属于你的、什么对你是有用的。通过这种行为,我们在不停地重修自己,它就像是消费行为的另一面。
简直,我们必须不停提醒自己一件事:垃圾并纷歧直是垃圾,它是我们生涯中的一些消费品,再往前,是工厂制造出来的器械,或者是这个器械的包装物、剩余物。我们不应该只看它酿成垃圾以后的事,恰恰要去看它的前身:它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会是这种附含垃圾、包装物的形态? 怎么到达用户与消费者那里?
若是我们把眼光放到生产厂商那里,就会知道,垃圾这么多一定不只是消费者的责任,物的形态和生产方式就注定了会有那么多垃圾会发生。
拾荒者的“老家”情结与“自由”
界面文化:《废品生涯》提到,拾荒者赚钱在都市,消费在家乡,“老家”是尊严、团圆与梦想实现的象征。拾荒者为什么选择以“老家”来重修自我认同呢?
张劼颖:首先要明确,任何的选择都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选择。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意识到任何人的选择都市面临结构性的限制,连他的想象也是受限的。
拾荒者作为城乡移民群体,没有大都市的户籍或是居留权,没有响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他们不太可能在打工的大都市留下来。与之响应的,他们的孩子没有设施在都市接受教育,或是加入高考。
我曾经接触到一个稀奇优异的孩子凭自己的起劲上了北京重点初中,但照样得回户籍所在地加入高考。而且随着都市政策的不停转变,可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念书的私立小学和幼儿园随时有被关停的风险,即便能在都市接受教育,也是阶段性的。这些结构性的限制决议了拾荒者几乎不会动“留下”的念头。实在他们和大都市的每一个通俗住民一样,都市面临这些结构性问题,只是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加倍严重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形成了一种很吊诡的生涯状态。
我们常说生涯在别处,他们的精神生涯就在老家。在冷水村,他们常年栖身在窄小的房屋内,外面是聚积的废品,冬天盥洗、洗衣,都要在室外用冷水,异常艰辛。他们在老家建二层小楼,或在县城买房,屋里的器械都是崭新的、家电齐全,异常清洁,可是没有人用,人人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人总要有寄托,老家就是这样一个寄托,他们也没有其余选择。他们总说自己终有一天要回去,事实上,老家也纷歧定回得去。
张劼颖在冷水村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指出,拾荒者口中的“自由”实在是异常“消极”的,只管理论上他们可以决议自己的事情时间,但实际上这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劳动,而无雇主、无组织的“自由”价值是无法享有许多基本权利。然而,许多拾荒者依旧选择用“自由”来形貌自己的职业,并把它看作主要的从业因素,你以为背后的缘故原由是什么?
张劼颖:我以为“自由”对每小我私家来说都很主要,这也再次说明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我第一次去冷水村,他们很一边很艰辛地捡垃圾,一边和我说干这行自由的时刻,我是很震撼的。那时刻我意识到,自由对我们每小我私家来说都是云云主要,真是“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我会说他们的自由实在是消极的,但这内里照样能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每小我私家都在结构性的限制之下尽可能地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让生涯变得加倍平安可控。只管拾荒者的劳动很艰辛,生涯条件很差,只管他们甚至要用尊严来换取这种看上去很有限的自由,但对一个小劳动者来说,天天钱能到手带来的平安感、对劳动过程的些许控制,都是很主要的。
作为劳动者的个体在承受着被异化、被高度控制的痛苦,众人皆是云云。但我们真的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以是一点点的自由都市显得很名贵,只管有时刻只是表面上的自由。
现在劳工研究越来越多地谈论不稳定的自由。许多人会以为,在家事情能从时间、空间高度不自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实际上,这种劳动形式可能是一种更大的克扣,或者说是资源更天真和自由的积累。你真正这样做之后会发现,事情和休息的时间、空间都是很难离开的,你甚至还需要自己支付装备成本。
谈论自由要看到两面。一方面,我们总是在被剥夺和控制的结构性处境之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总是试图去控制点什么、捉住点什么,不惜去用其余器械来换取自由。拾荒者的故事对照极端,由于除了艰辛的劳动之外,他们还在用尊严换取自由,由于处置的是垃圾,加倍容易被歧视和污名化,这是在几乎没有选择的情形下他们用主观能动性去控制自己生涯的起劲。
环卫工人与拾荒者的模糊界限
界面文化:《废品生涯》关注了与拾荒者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人群的生涯,例如黑车司机、装修散工等,但没太誊写环卫工人。这个群体也站在垃圾处置的前线,直接接触垃圾,他们与拾荒者的事情有交叠、交织,而且形成“有制服”与“无制服”的对比,你对这个群体有过考察或是思索吗?他们和拾荒者有什么差别?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劼颖: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有关环卫工人的文章。环卫工人是市政设施、市政系统、收运系统和通俗住民之间的界面,也是人和垃圾之间的中介。环卫工人是决议垃圾分类成败要害一环,然则他们太卑微了,太不可见了,经常被我们忽视。
环卫工人也是垃圾的直接接触者,但他们一样平常是劳务派遣,这和拾荒者差别。拾荒者是自觉地在非正式经济地带里寻找生气,而环卫工人是正式的,只管属于劳务派遣工,但他们也是市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门。
但环卫工人和拾荒者之间的界线又是模糊的,许多环卫工人也在收卖废品。好比说在我考察的地方,环卫工人会一边清扫,一边把值钱的器械收攒起来,然后拿去卖掉。他们具有厚实的垃圾分类、资源接纳和再用知识,他们很懂市场。但我不敢说所有的环卫工人都是这样。
一旦最先执行垃圾分类,会不会触动到他们的利益?差别社区的详细行动纷歧样,至少在我看的案例内里,若是住民能做好垃圾分类,他们可以更方便地收卖,实在是双赢的。
界面文化:我们知道拾荒者可能会“包小区”,那他们与小区牢固的环卫工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张劼颖:有许多种可能。首先要说,废品接纳也像生态链一样,有的生物取走大的部门,有的取走较小的剩余物,垃圾接纳也要经由好几轮,并不是一次性拿走那么简朴。最最先,住民可能会把一些最值钱的器械卖给废品接纳者,其余部门扔掉之后,又有人来一次次分拣,分拣到最后就剩下一些很噜苏的器械。好比一个玻璃瓶上的金属盖,拾荒者网络好几百个再拿去卖,他们的事情实在相当精致,而且需要大量的积累。经由他们处置,琐屑的其他垃圾又酿成了可以被接纳行使的资源。
拾荒者和环卫工人之间可能有多种关系。有人是身兼二职,穿上制服是环卫工人,脱下制服又成为拾荒者;有些拾荒者和环卫工人之间是互助关系,也有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是竞争关系。
科技与市场能改善废品接纳与拾荒者的现状吗?
界面文化:现在有些小区内里会看到一些智能废品分类接纳柜,你以为这种科技的运用是否会打击拾荒者群体呢?
张劼颖:老实说我以为这个器械没什么用,现在看来,这些智能柜的宣传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意义。
若是一项手艺实现了现有市场无法执行的功效,或是以一种更好、更高效、更环保、更人性化的方式实现,我们就会说这项手艺是有价值的。但现在我所看到的大部门智能接纳柜接纳的器械原本就有人处置了,像塑料瓶一类,放在一边,环卫工人或者拾荒者都市收走。它并没有扩大资源接纳的局限,也没有做到更精致化,似乎也没有给人们分类提供更强的做垃圾分类的动力或者激励。机械自己就酿成了垃圾、装饰,摆在那里虚耗空间。可能相对对照有用的是旧衣接纳箱。旧衣接纳太廉价,环卫工人和拾荒者都不太愿意做。现在有了旧衣接纳箱,有人愿意把旧衣物集中放进去,而不是直接酿成垃圾。
之前我看到一个还不太成熟的手艺,它是家用的厨余垃圾堆肥机,若是这项手艺可以和家庭生涯很好地连系,占用空间小、能耗很小,无稀奇异味,那可能就可以有用解决厨余的问题。我期待能有这种真正的智能性手艺泛起。
界面文化:近年来也泛起了不少废品接纳创业公司,也有一些原来的拾荒者介入其中,甚至是创业合伙人,《财新周刊》就曾报道过老徐的故事:1991年,老徐和许多河南老乡一样,到北京踩着三轮做废品接纳,二十余年间也履历了废品接纳人从市中心逐渐向郊区后撤的浪潮,2014年,老徐和儿子将重心从废品接纳转向垃圾分类,走上创业之路。老徐父子的故事是否暗示着拾荒者未来生长的新可能呢?这些“散兵游勇”的劳动者是否可能被重新纳入市场化组织呢?
张劼颖:收编的事之前也有过探讨。收编纷歧定是雇佣关系,也可以是互助。收编的形式和水平可以多样化,依据当地栖身空间的详细治理情形来决议。
历史履历解释,收编有难度,由于拾荒者是很天真的,他们也习惯一种天真的事情方式,他们的事情地址、时间随时都在更改。收编过程中可以不要管得太死,若是你把他框死了,完全酿成环卫工人那种雇佣关系,一方面不太现实,另一方面他们事情的天真性和细微性优势就无法施展出来。好的收编方案应当既给他们一个正式饭碗,又确保一定天真度。
垃圾分类接纳,需要系统作为也需要个体担责
界面文化:北京从5月1日起正式施行生涯垃圾周全强制分类,你的小我私家体验若何?你栖身的小区是怎么做的?
张劼颖:这个事情正在履历被高度谈论的阶段。不管做不做垃圾分类,人人碰头都市说这个事。在这种情形下,垃圾分类问题至少变得可见了,那么接下来的执行就很要害。若是没有什么实质行动的话,人人被调动起来的注意力就会逐渐消失,这是很可惜的,也是一种虚耗。
界面文化:你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提到,在做调研的时刻,许多人跟你说:“我们分好的垃圾,许多也被环卫工混起来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张劼颖:这件事要从两方面来看待。一个是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垃圾处置系统确实存在前后端不匹配的问题。作为住民,我们会去想垃圾分类是为了什么、分类之后垃圾去了那里、怎么样被处置等等。若是垃圾分类的中后端处置没有获得很好的宣传,甚至基本不配套,住民很容易对当下做的事发生嫌疑。垃圾分类需要给通俗市民一幅全图景,让人知道前因后果。只有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而且真的有这样配套的设施和系统,才气更好地激励住民举行垃圾分类。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垃圾分类不只是一个小我私家行动的问题。一些环保宣传教育之以是失败或者不够乐成,之以是让人感应疲劳、虚伪,很大的缘故原由在于把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小我私家化了,总以为环境欠好就只是个体罪责的堆加:由于你的生涯不够环保、你做得不够好,以是才泛起了灾难性的环境问题。一样平常来说,有责任感、有知己的通俗人听到这样的论调后,都市发生一定水平的认同和愧疚,以为自己应该做出改变。但人人很快就会隐约感觉到,整个系统似乎没有真的在做垃圾分类,因而我自己的起劲是无效的,信心就此被消逝。环保宣传教育若是把系统性的问题完全小我私家化,反而晦气。
我们说垃圾治理系统自己要拿出诚意来,要有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后端配套设施,这样才气给住民信心,分类才有意义。但强调系统性、结构性并不意味着作废个体的责任。“我做垃圾分类也没用”这种话,我听过太多,在某种水平上这是推卸责任,语言人可能基本没有亲眼瞥见垃圾被环卫工人混起来,只是耳食之闻,简直有点都市传说的味道了。
昨天我还在我家楼下瞥见环卫工人在做厨余垃圾的破袋,还用夹子把厨余垃圾里的其他垃圾分拣出来,他们实在是在做垃圾分类,而不是像人人说的一样把住民分好的混起来。固然,我不否认这个系统另有许多罅漏之处,有一部门确实没做到分类收运,但也存在环卫工人替你分类的情形。可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们没有做垃圾分类,是环卫工人在做”这种说法呢?一些人在说“我分好的垃圾又被环卫工人混起来”时,他们真的做了吗?照样没做,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在道德上没这么难看?
我始终以为建设优越的系统是第一的,其次,每小我私家是有责任的。若是前后端相互张望、相互指责,没有人迈出一步的话,垃圾分类就会一直是个死局、僵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能做的是全力去讲清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前因后果,把图景弥补完整,让住民获得更多的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判断选择。现在的垃圾分类宣传把故事截断了,看不见前面也看不见后面,只是告诉人人,你专一做好这一块就行,这是异常武断的。作废人主观能动性的环保宣传教育是很难乐成的。
界面文化:现在的环保宣传里通常就只有两幅图,一幅是我们的环境若何糟糕、我们应该怎么样举行垃圾分类,下一幅就就直接跳到被净化后的绿水青山,中心的许多曲折起劲都被省略了。“环卫工人混运垃圾”这种说法也忽视了环卫工人正在负担被转嫁的劳动和责任这一事实。
张劼颖: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残缺的拼图,需要通过多方互助的实地调研和叙述才气把拼图补全。
许多人在指责环卫工人的时刻没有看到他们实在是在替我们劳动,这也是一个群体间关系或者认知的问题。对都市运作来说,拾荒者、环卫工人功不可没,但他们又是隐形的。人人要么无视他们,要么歧视他们,或者以为他们离自己越远越好,又或者是对偶然曝光的悲凉个体表现出戏剧化的同情和同情,热搜一阵、转发一阵就过去了。然则我们有没有系统性地想过,拾荒、环卫环保也是一份事情,这些人群的逆境不是“可怜”,而是合理的权益无法获得保障?
做社会科学研究,我以为自己需要一点道德追求,对公平和正义有期许。带着这种感动走进冷水村,难免会受到打击,发生同情,但只有暂时把情绪感动搁在一边,去挖掘背后的缘故原由和机制,才气做到“不止于同情”,去尊重别人的主体性。
《废品生涯: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胡嘉明 张劼颖 著
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
界面文化:当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甩掉文化改变了人类和物之间以往的关系,很少有物再成为情绪和影象的载体。好比说一个盐罐,我外婆用了几十年也没有扔掉,但这些小物件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就是迁居时可以被甩掉和精简掉的,更不要说外卖盒、快递盒,到了手里很快就会酿成垃圾。无论是垃圾分类接纳难,照样拾荒者所遭受的污名化,都与这种对“物”和“垃圾”的单调认知有关。我们应当若何重新建构人与物品、垃圾之间的关系呢?
张劼颖:我们对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照样应该多一些想象力。你说的老物件是一种,若是我们对物有更多的情绪和联系,也是削减垃圾制造的一个好的设施。另有一种思绪对照像人世释教和一些环保组织讲的惜福爱物:每一个“物”都来之不易,它是地球上的某种资源,内里可能也凝结了别人的劳动,人应当学会珍惜。我并不想张扬某种宗教,但人人可以用更多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和物之间的关系,宗教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怀旧的也好,怎么样都好,总之是可以多一点想象力,多一点看待物的眼光,不要只是很单一的、没有情绪的“用完即弃”。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cms/2020/0528/1982.html